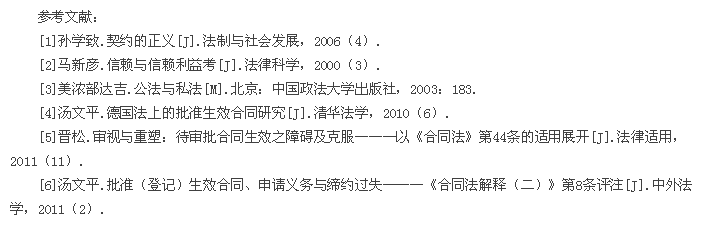简述法定未生效合同的正当性根据与批准、登记行为
发布时间:2019-1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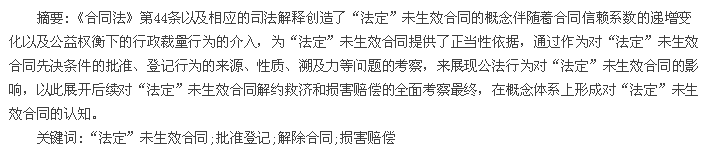
私法与公法二元化的分野,使整个社会似乎存在着两个清晰无涉的场域,但整个社会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整体,私法与公法间必然存在着逻辑管道使二者彼此进入,整个法律体系互为一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52条第5款以及《合同法》第44条第2款均为《合同法》留给公法的管道。《合同法》第52条第5款“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认定合同无效,作为公法中效力性强制规定直接介入合同领域的佐证,判定当事人作为合意结果的合同是否自始、绝对、终局的无效,这是一种对有效成立的合同“不适法”性的绝对静态评价。相对于《合同法》第52条第5款的绝对静态评价而言,《合同法》第44条第2款中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作为公法裁量权的介入管道,是一种动态化的评价机制,与《合同法》52条第5款静态评价机制形成有机衔接。合同成立、生效二分的做法源自德国法,后为日本及我国所采取,进而在直观层面上合同的“生命历程”被划分为三阶段:成立前、成立后生效前、生效后,“法定”未生效合同的产生时间阶段即为成立后生效前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段。我国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一)》第9条,首次区分出合同“未生效力”的概念,将公法中“批准、登记”之具体行政行为引入作为私法重要场域的合同效力评价机制之中,由此对于该管道设置正确与否、合同效力样态的争议以及合同效力各种机制的适用无不拷问着“法定”未生效合同这一概念法学下衍生的产物。本文力求通过针对《合同法》第44条的剖析完成对“法定”未生效合同概念的重新认知。
一、“法定”未生效合同的正当性根据
合同是双方当事人以法效意思为核心的合意的展现,其背后是内心彼此的信赖。作为法定条件的“批准、登记”又为已成立的合同提供了公法性政策合同效力,运用具体行政裁量行为在私法领域中实现公法所要实现的公共利益之保障,都为“法定”未生效合同提供了正当性依据。
(一)信赖因子在“法定”未生效合同中的存在指数。
“法定”未生效合为成立后之合同,具备了合同最基本的合意要素。当事人双方的意思表示是赋予合同以法律拘束力的根本力量;只要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明令禁止的无效合同的情形,合同作为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成债权发生根据的正当性。合意给予了合同最基本的拘束力,这也导致了一方以法效为核心的意思表示必然产生相对方之信赖,合意是双重信赖之迭加。信赖,是指当事人相信要约或合同而为准备签订合同、准备履行合同或履行合同的行为(包括作为或不作为)所导致的财产减少和与他人订约机会的丧失。
《合同法》第44条第2款的规定,将合同成立与生效时间点拉开,显然当事人对合同成立与生效的信赖系数是由存在合同拘束力的信赖状态到合同效力充分运行的完全信赖状态的演变。对于成立后的合同会产生无效合同、可撤销(可变更)合同、效力待定合同以及未生效合同四种样态,而四种合同与合同成立、合同成效之间是一种非线性结构,故此四种合同样态的横向可比性相当困难而且无实益。“法定”未生效合同和合同成立与生效呈纵向线性结构,此时的信赖系数的根本影响因素为:当事人的心理预期。对于批准尤其行政法上的审批,《行政许可法》最终采取的是“同一说”,即认为行政审批就是行政许可,应受《行政许可法》的约束。故一般审批与登记为特殊行业以及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秩序之重大事项,当事人应该预见相关批准、登记事宜,此时的合同信赖系数应当高于合同成立时以及之前的阶段但低于合同生效时以及之后的阶段。从合同信赖法锁的角度,在公法注入的情况下,信赖系数存在递增性,“法定”未生效合同机制的引入便对这一特殊信赖阶段予以了充分保障。
(二)公益因子在“法定”未生效合同中的存在价值
在现代法制背景下,应该积极强调公私法的分野,但是二者不是全然隔离与封闭发展的,必须在公私法自身的概念体系中设置管道,使双方适当的流入来激发与保障自身的活力。《合同法》第52条第5款与第44条第2款即为合同法为公法设置的管道,前者为合同效力绝对终极无效否定之管道,后者则是合同效力给予政策与公益行政自由裁量之管道,二者相依相偎,尤其后者需要行政裁量行为在合同法中的引入问题十分重要且复杂。公益因子对行政裁量行为的决定性也导致了其在“法定”未生效合同的根本价值所在。
二、“法定”未生效合同中的批准、登记行为
“法定”未生效合同的批准、登记行为是未生效合同的起因,但法定批准、登记行为独立于未生效合同本身。“法定”未生效合同的批准、登记行为为合同生效与否的决定性因素,而这种决定性因素本身是公法裁量性规则的运用,其直接作为未生效合同的先决条件决定着合同的命运,所以批准、登记要求是一种与“法定”未生效合同有着相关性但独立于当事人合意的法定条件。根据《合同法解释(一)》第9条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我国《合同法》将批准登记的时间推迟到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这是一种事后批准。作为公法之行为的批准、登记是否在《合同法》第44条环境下存在“法定”未生效合同效力溯及力的补正的可能性即由第2款成立后至合同经过批准、登记回复到第1款所确立的自成立时生效的时间点上。对于此点,笔者认为,在《合同法》第44条下应该否定批准、登记行为对合同效力前移的可能性,否定合同效力的溯及力,当批准、登记行为完结时合同生效与否的时间点才应开始计算。
批准、登记行为的瑕疵是否会对“法定”未生效合同生效之后形成影响不无疑问。批准、登记的瑕疵存在着两种情况:一是虚假行为,是指当事人存在主观故意或过失且违反了法定义务(及时、完整、真实地披露、报送法律规定的批准、登记所需的重要事项的义务)造成已进行批准、登记的事项与事实不符的情况;二是错误行为,因批准、登记机关过错使已进行批准、登记的事项与事实不符的情况。在瑕疵批准、登记后未生效合同成为生效合同,不应存在合同撤销之可能性,可以采取行政法上的其他补救措施,但存在提请批准的合同更正的可能性。《合同法》第55条关于无效合同的规定已经对害及公共利益以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合同进行了屏蔽,而《合同法》第44条所涉及的公法裁量性规范虽涉及地方政策和某种侧面的公共利益,但不至于损及根本生活秩序,在作为私法的《合同法》中进行公私法法益衡量,理应选择对当事人合同下的合意以及信赖进行保护。与此同时,可以对虚假批准、登当事人进行行政法上的处罚,使其在错误的程度范围内承担责任,很有可能合同利益小于或等于其惩罚数额,但仍旧保障了合同另一方当事人之信赖,保障了行政行为下合同善意第三人。在批准、登记行为瑕疵情况下仍旧存在对提请批准的合同变更的可能性,即对合同进行合理的调整,这种调整并非仅指非实质性变更、纯形式变更,在有限的程度上须接受一定削减,不过在另一方面,变更后的合同也给同意变更当事方带去一些利益,并且使合同构造被同意或者免予同意要求,并且结合意旨、目标和内容做综合评估的话,这一新的合同构造也十分靠近初始的缔约目的。
三、违反批准、登记义务的合同救济
“法定”未生效合同的特殊性必然也导致了合同救济的特殊性。《合同法解释(二)》中第8条规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经批准或者登记才能生效的合同成立后,有义务办理申请批准或者申请登记等手续的一方当事人未按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办理申请批准或者未申请登记的,属于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规定的‘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相对人的请求,判决相对人自己办理先关手续。”这是批准、登记行为替代履行的规定,由此推及申请批准、登记义务人必然存在直接履行的义务。但是此种实际履行仅为申请义务的实际履行,并不是批准后生效合同的给付义务。批准、登记行为即为“法定”未生效合同的控制性因素,未生效合同的全面实际履行必须满足此前提条件,所以在“法定”未生效合同的情况下并不存在合同救济中的实际履行方式的运用。在此特殊阶段,合同救济方式中的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在“法定”未生效合同中存在着可能性。
(一)解除合同的适用
“法定”未生效合同本身存在一段成立与生效间的特殊阶段,此时如若审批、登记义务人不履行批准、登记行为,而合同相对人的替代履行又存在障碍,就会产生一个几乎永远不能被治愈的而未生效合同形态存在。在“法定”未生效合同下,当然存在着由于合同成立产生的足以影响合同主给付义务的从给付义务、附随义务的履行,所以在“法定”未生效合同中应该适用合同解除这一救济方式。按照正常的合同救济理论解除合同存在于合同生效后,从解释论的立场,在现行法上找到法律依据使合同解除权存在于“法定”未生效合同中尤为迫切。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中第6条第2款规定“转让方和外商投资企业拒不根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报批义务,受让方另行起诉,请求解除合同并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显然,最高法院在“法定”未生效合同中给予了当事人合同解除权,但对于其他需要审批、登记的合同能否扩张适用,应该找到《合同法》上的根本依据。《合同法》第94条第2款“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这是合同法定解除权中预期违约的规定,对于“在履行期限届满前”此时间段的解读完全可以将其扩展到合同成立后到履行期限届满前,由此合同解除权便可存在于“法定”未生效合同中。
(二)损害赔偿的适用
“法定”未生效合同中批准、登记行为义务人的损害赔偿责任究竟是一种缔约过失责任还是一种违约责任抑或是一种特殊形态的融合,这种层次的厘定对责任的构成要件以及赔偿范围的确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合同法解释(二)》第8条规定的赔偿范围为“由此产生的费用和给相对人造成的实际损失”,以此理解,赔偿损失的范围除了为准备合同的相关费用外,还包括期待利益损失。这决定了“法定”未生效合同中的赔偿责任既具备了缔约过失责任的成分也具有违约责任的成分。假如若非这一缔约过失行为该法律行为就会按受害人期待的内容实际成立,或者受害义务的保护目的含相关要求的话,该损害赔偿请求权可以例外的延伸至履行利益。
就此看来“法定”未生效合同的损害赔偿样态是一种特殊的融合状态。缔约过失责任在我国合同法中是一种过错责任,而恰恰相反违约责任则是一种严格责任,这就会使“法定”未生效合同的损害赔偿要件的构成产生混乱。如何避免此种局面,其方法在立法论上无非是使违约与缔约过失责任原则统合起来,至于当前解释论上的对策应该寻求价值衡量,如果是审批、登记难度大以及签订合同时义务人之主观不存恶意以及重大过失此时倾向于缔约过失责任赔偿样态,反之则宜确定为违约责任的赔偿样态。区分不同情况而言,在合同相对方仅诉请义务人履行报批义务并赔偿损失的,此时损失的赔偿范围应限于信赖利益的损失赔偿;在义务人不履行合同报批义务致使合同未能生效而不能履行的,此情况下解除合同赔偿范围应该以履行利益为限,不宜将可得利益包含在内。
结语
《合同法》第44条为行政裁量性行为提供了注入私法的管道,形成了“法定”未生效合同的概念。“法定”未生效合同的概念在精确化法律体系中产生了不小的争议,而且其具体效力内容对比成立合同与生效合同存在着相应的模糊性,这就需要对“法定”未生效合同的概念进行细化认知。“法定”未生效合同为由合同成立到合同生效的阶段的信赖系数的演变的产物以及为公法法益裁量性行为的介入提供了合同机制在这一特殊阶段的存在场域。作为“法定”未生效合同关键性因素但又独立于“法定”未生效合同的批准、登记行为义务的来源、性质、溯及力问题以及瑕疵对合同本身的影响的细化是“法定”未生效合同效力展开的前提。对于作为私法形成性行政行为的审批、登记的考察应该从公法的角度进行分析,但对于作为私法的合同法中公法之注入更应该关注公法行为对合同私的信赖之锁的影响,使固有合同机制在“法定”未生效合同中得到充分运行。
当合同的运行产生障碍时,合同的救济机制则凸显出来,“法定”未生效合同应该在批准、登记义务人不履行义务并且合同相对人存在自己履行障碍的情况下赋予合同相对人以解除合同的权利,并且可以主张损害赔偿。但这种损害赔偿是一种既融合了缔约过失责任性质又包含了违约责任性质的混合状态,所以在构成要件上应进行选择性衡量,并且区分具体情况在“法定”未生效合同中区别使用信赖利益损害赔偿以及期待利益损害赔偿。